论文学社交圈的认可度,爱尔兰姑娘萨利·鲁尼被类比成当代的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是有道理的。她在2017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聊天记录》,翌年,她的第二本长篇《普通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即将播出的BBC版12集电视剧“忠实地、逐页地”改编了原作,要知道,上一次让BBC翻拍时“逐页改编”的小说是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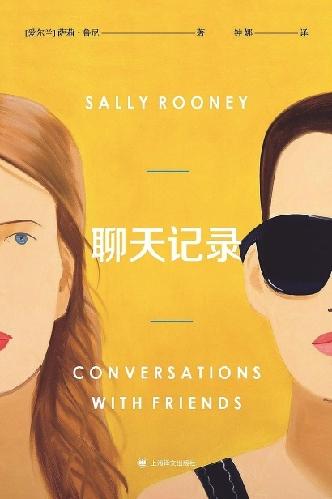
英国《卫报》的书评专栏作者说,把刚出道的作家比作菲茨杰拉德或塞林格,有点不吉利,想想菲茨杰拉德盛年沉沦于名利场,去好莱坞之后被不断打击,短暂的一生受困于酒精和挫败;塞林格早早地自绝于文学圈,深居简出,如果没有他儿子,我们将永远读不到他后半生面向内心的文字。给声名鹊起的年轻人贴上“当代菲茨杰拉德”或“女版塞林格”的标签,简直是诅咒。但市场需要,“迷惘的一代酗酒,垮掉的一代嗑药,鲁尼的千禧一代沉迷于App和聊天软件,社交网络是这代人的酒精和大麻”,诸如此类的口号很有助销量。
青春写作,被铭记与被遗忘的
鲁尼是个聪明冷静的姑娘,她在接受英国记者的访谈里有段话说得漂亮:“除了我自己,我不能给任何人代言。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就够难的。我不介意我的小说因为技术不够好而被差评,但不能接受‘它失败是因为它没能说出一代人的心声’,我压根没有这想法。”
在时代的语境中讨论当代作品,或时过境迁以后,把特定的作品放置在特定语境中考量,这是常见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文学经纪人卡罗琳娜·萨顿有不同的看法。她回顾自己的职业经验:“每当一批新的写作者出现,被重视的总是他们对当代生活的具象呈现,作品发布的背景,以及是否传达不同于前一代人的价值观念,而修辞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其实,“决定一部作品力度和可流传度的,从来不是种族、阶层、性别这些争议议题。”《纽约客》的小说编辑黛博拉·翠斯曼给出同样的观点。1997年以来,翠斯曼平均每周要面对200-300份投稿,“能让一个作者脱颖而出的,从来不是他/她能否正面强攻时代议题,而是处理素材的技法。”
来看这些曾被贴过“代际代言”标签的作家和作品:菲茨杰拉德的成名作《人间天堂》,写公子哥埃默里的骄傲和迷茫;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里,迪安是浪荡儿,而叙述人萨尔是心灰意冷的布尔乔亚体面小伙儿;B·E·埃利斯在21岁以《比零还少》震惊英美文坛,小说主角是一群洛杉矶的阔少们,在极度丰富的物质环境中被异化成群鬼;扎迪·史密斯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写出了《白牙》,这本“怀着巨大野心写成”的作品里,混血姑娘艾丽目睹了移民熔炉的伦敦郊外社区里,几个中产之家离乡背井后的剥离、颠覆和拔根而起的痛苦重生。
把鲁尼的《聊天记录》和《普通人》放到上述作品的集合中讨论,它们的共同点除了“青春书写”这顶大而化之的帽子,更明确的共性在于小说的主角不是“时代的大多数”,作天作地的姑娘小伙儿们出身非富即贵,享受着“何不食肉糜”的既得利益和幸存偏差,仍然过不好他们的前半生。阶层跃升的焦虑、结构不公的伤害以及性别平权的抗争,这些在任何时代都属于正统的议题,在这些杰作中却是缺席的。
反而是一些在出版时被认为“代言发声”的作品,飞快地被挤出文学的会客厅。《沙丁鱼之日》里一筹莫展的英国矿区男孩,才是1950-60年代集体绝望的年轻人的缩影;《伯格》出版时,作者安妮·奎因被盛赞“用贝克特式的笔法写出了英国劳工阶层年轻人的呐喊”;埃德娜·奥布莱恩的《乡村姑娘》极罕见地刻画了1960年代爱尔兰村镇少女“长大成人”的过程,但这部作品一直被划归成乡土文学的样本……这些昔日的“时代横截面”,随着时代的翻篇而翻篇了。
在文学作品里寻找“一代人”是一种几乎肯定会失败的企图,因为在文学的功能里,没有为集体代言这一项。正如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讲里说: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总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与个体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中间人。历史需要的代言人不会喜欢艺术和文学,因为文学越是出色,就和充满重复的生活之间区别越大。
用传统的方式书写当代细节
布罗茨基提出“在文学中,美学先于伦理”这个观点时,谈到艺术的发展意味着创作者不断为素材找到新的美学解答。
从菲茨杰拉德到凯鲁亚克,从琼·迪迪恩到埃利斯,即便作者本人当时未必有文体实验的自觉,以事后之明来看,“小说”的宏观框架和微观技法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完成一轮接一轮的变异。
埃利斯本人最近自卖自夸地谈了谈《比零还少》。他回忆,当年的创作出于单纯的逆反心理:能不能有一种青春文学就“写青春的困惑和麻木”,既不是人生启示录,也不是道德训诫剧?35年过去了,他重读这本小说,觉得“公子哥的花式作死情节”不值一提,而它的可读性甚至与内容毫无关系,“用反情节的笔法,写出无所事事的无聊情境里巨大的张力。”
细读《聊天记录》和《普通人》,会发现“寻找小说新美学”的文体焦虑在这两部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两部作品给人的直观第一印象,在于极简主义的文本,直白,准确,没有花哨的修辞,符合当代的“无印良品”美学,用简洁定义一种新的优雅。作者用干净的修辞从容地铺陈细节,小说的可读性在于细节的组合和节奏,这是一场很慢的检视,愉悦来自于被遮蔽的细节逐渐地被发现。可以理解BBC在改编拍摄《普通人》时不愿删去任何内容,因为叙事里好看的、独特的,全是文学少女视角下的当代生活细节——年轻的、富足的、网生代的。
埃利斯觉得《聊天记录》“没意思”的地方,恰恰让很多写作者和评论家如释重负:萨利·鲁尼让人们看到,小说这门形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哪怕是19世纪的路径,也还走得下去。最初发表鲁尼的短篇小说的编辑说:“我们觉得她写得好,就是因为她没有石破天惊的‘新’。我喜欢她塑造人物的生动感,以及人物关系中充满生命力的流动感,她敏锐地感受着两性关系中的粗暴和脆弱、控制和反控制,这些在19世纪小说中就存在了,区别只在于那时的男女主角写信,现在他们发短信。她的文本成为一种文学的证明,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处理这个时代的细节,仍然是奏效的。”(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