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利希蒂希︱本·勒纳的自传体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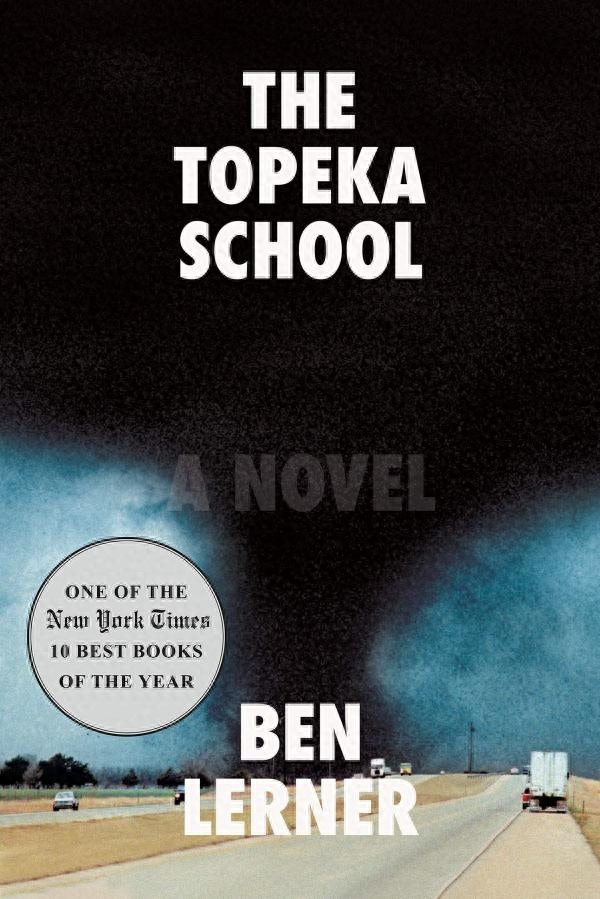
THE TOPEKA SCHOOL. Ben Lerner. 282pp. Granta. £16.99.
正如菲利普·拉金说他自己那样,大部分的写作者都不会“连环屠龙”。在他们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之后,一个人的文学生活就可以与另一个人进行比较:能够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以及思考写作的时间;在校园里写作,或者如果幸运的话,在异国他乡的文学艺术节里写作。对于自传体小说及其附属题材的创作者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挑战:在已经充分发掘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之后,如何避免无休止重复制造处于狭隘的社会背景中的相同的叙事?对于某些人来说,答案是没法避免。也许这足以驱动他们重写早年的作品(例如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或者也有人可以为了追求真实的目的而与乏味斗争,用尽所有内容,包括厨房水槽的描述在内,以耗尽文学的可能性(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或者也有人会去写一本名为《悲伤的年轻文学人》的小说(基思·格森);或者还有人会利用这种体裁,作为思考作者对母性的矛盾情绪的一种方式(席拉·赫蒂);或者认为创造“角色”已经不再适合我们此时的文化时刻(蕾切尔·卡斯克);或者就充分利用公费出国旅游来为自己的创作提供背景和叙事追求(杰夫·戴尔)。自传体小说及其技巧具有令人愉悦的延展性。但这仍然会是一个贫乏的——而且在政治上令人不安的——文学领域,它只能为我们描绘那些创作者的成长过程以及成为作家后的画像。
本·勒纳的头两部小说是经典的现代自传体小说。《离开阿托查车站》(Leaving the Atocha Station,2011年)描述了一个不谙世事的美国青年诗人亚当·戈顿(勒纳本人隐藏在一层宛如保鲜膜似的伪装后面,所以我们只能相信如此),在某个项目资助下游荡于马德里。他服食药品、阅读书籍、反躬自省(参见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诗人自渎”);他的西班牙语很差劲,于是他常常处于误解,尤其是通过想象而进一步丰富的误解之中;他试图用自己的诗句和谎言打动女性。在如此题材的基础上,《离开阿托查车站》以其质量给了我们最大的惊喜。勒纳(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展现了自己是一位具备敏锐观察力、灵巧控制力和诱人智慧的小说家。他开启了一个令人愉悦——即便是其中的模糊朦胧也令人愉悦——的空间,介乎于他作为一个精明但又不老练的叙述者的自言自语和表达他作为创作者的声音之间,调和于自我厌恶和自我迷恋的恰当平衡之中。

《离开阿托查车站》
在他随后问世的《10:04》(2014年)中,勒纳在拓展自己的创作能力的同时,攀上了后设小说的表面。亚当·戈顿成为了本·勒纳,一位刚刚收到一大笔订金来创作他的第二本小说《10:04》的小说家。这个版本的勒纳比他之前的化身更加成熟,但同样内省。他在纽约(以及得克萨斯州)四处闲逛,思考着自己的艺术,并为世界而忧虑。他正试图通过人工授精使他的朋友怀孕。与《离开阿托查车站》一样,尽管表面上看似内容狭隘,但仍有许多故事发展:精细描绘的聚会或医院探病的片段;关于约翰·阿什伯里和艺术家克里斯蒂安·马克雷的令人愉悦的题外话(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是真的题外话);关于精子捐赠的考虑,以及主人公本对成为父亲的不安,产生了某种更加广泛的紧张情绪;源自电影《回到未来》的一个有益的延伸比喻。这是一个关于多种未来,多种可能性的故事。也许值得留意的是,现实中的勒纳是两个孩子的已婚父亲,而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书中关于人工授精的线索并非虚构;某个从未发生过的未来——尽管无论怎样这都没有关系。正如本在《10:04》中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喜欢诗歌,部分理由是因为小说与非小说之间没有区别”。
这两本书中,尽管有明显的自我审视的成分——部分是通过其幽默的效果——勒纳表现了自传体小说并不一定自恋的某种实践:亚当/本这两个人物不是卸下包裹的货车,而是穿越其它一切的导航船。而这“一切”包括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世界:他在《离开阿托查车站》中穿越了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愤怒,以及对2004年马德里基地组织爆炸案的恐惧。在《10:04》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被超级风暴和社会动荡所包围的纽约。但是,自传体小说有其局限性。勒纳本人曾经评论过《10:04》可能获得的反响:“哦,又来了一本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写的布鲁克林小说。”
在《托皮卡学校》中,他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和范围,将我们带离了那个自由主义的大都市和某个属于单一意识的领域(或者说,汽车驾驶席)。他打出了一张尚未使用的王牌来实现这一目标:挖掘他的童年。他也展示了他在《离开阿托查车站》中描述过的事(有趣的是,他试图以此解释他对西班牙语的误解:“我在她的话里想出了几个可能的故事”),以此来展示他所具备的“在多个世界中和谐思考”的能力。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像传统小说家一样,居住在其他人的思想和声音中。我们仍在勒纳的土地上:处在亚当·戈顿(对原始自我角色的回归)在现代的布鲁克林那本书的框架中:这本小说就在我们手中。但是大多数行为发生于1990年代,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勒纳/亚当成长的地方),并且以多种模式、多个角色的视角进行叙述:亚当(以第一和第三人称形式出现);他的母亲简(第一人称,在某一章节中她喊了一声“你”,指向成年的亚当);亚当的父亲乔纳森(第一人称);以及亚当的老同学达伦,在每个漫长的章节开始时,都有短短一段斜体字讲述他在第三人称下的故事。整部小说的结构很出色:主要章节是独立的情节,或微型回忆录,在主题上而非时序上相互回响,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空间。同时,达伦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头以在警署审讯室中开始,他承认用一枚桌球的母球犯下了暴力行为,然后从我们在破碎零散的片段中,跟随他从幼年至今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线性的线索,最终呈现为小说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0:04》
在某些方面,《托皮卡学校》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简单家庭故事,创造性地展现了两对父母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这些角色的世界。书中的十几岁的亚当——勤奋,有才华,敏感但又不成熟,冲动而咄咄逼人。他正努力成为一个成年男子,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努力提高自己,同时又陷入自由与智性的家庭生活环境与在保守的堪萨斯州环境中其他好斗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他是一位出色的辩论队成员和坚定的举重运动员。他认真地为女友带来欢愉,并上网学习技巧。他希望能够有卓越成就,让自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在精彩的开幕篇章中,他和女友安伯在湖里的一条船上;时间是晚上,他们正在享受一瓶南方安逸利口酒。“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说话。当他转身去看看他那番话的效果时,她已经不见了,牛仔裤和毛衣堆成一堆,与烟斗和打火机放在一起。”比起恐慌更加奇怪的是,他划船回到岸边,从那里一路飞奔到她的住处,推开滑动门爬到楼上。只是,那并不是她的房子(湖周围的所有房子看起来都一样)。他成为了一名闯入者——第一个对象是安伯,他的男性说教把她赶下了船,而现在的对象则是这个陌生人的房子,他在那里的徘徊变成了小说家的错位、出窍的徘徊。这一段的故事讲述可谓讨喜(紧张而有趣);它也与本书更广泛的主题相呼应。
亚当的母亲简是一位心理学家,撰写有关家庭和婚姻的临床心理学畅销书。她富有同理与同情心、聪明、直率、无拘无束。她那个“欺负她的儿子”(她自己的话)并不是她的生活中唯一一个难以忍受的男性。还有她的(温柔的,大部分时候支持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失落男孩问题专家”)以及他的“忠贞情怀”;她在“基金会”的嫉妒的同事觉得她太受欢迎,并以“雄性奋斗”(此时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的指控抹杀了她的女权主义课题;有“男人们”经常打电话到简的家里,然后以污言秽语大声辱骂,指责她是婚姻破坏者(他们的妻子读了她的书);还有她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多年以前曾犯下过一次虐待行为,其影响仍在回荡。简是小说的道德中心(乔纳森的性格着笔不多)。她也是低声私语时的胜利者。当她将亚当辩论比赛中一位令人讨厌的参赛者形容为“迷失在她的对手中的过时美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正是她会观察到的。
就贯穿全书的隐喻而言,辩论赛无论在结构上(提供内在的叙事,再加上内在的话语内容)和主题上都是巧妙的手段。在一开始,勒纳就向我们介绍了“高速发言”的概念:这是一种用于辩论的技巧,力求以论点的数量——而不是说服力——来压制对手,“规则是……‘放弃论述’,不管论点的质量、内容如何,都应予以承认”。这显然与辩论的精神背道而驰(“它使政策辩论脱离了现实世界”),但它也被视为时代的标志(“企业人员一直在应用某种版本的这种辩论技巧”),同时也预示了几十余年后的今天,四十岁的亚当/本正在写他的书:信息超载、政治措辞杂糅、对公共话语的刻意混淆,与现实脱节的语言。
如果说《托皮卡学校》所实现的众多奇迹之一是其丰富的理念得到精心布置,并互相交织,相互强化的方式(在一次辩论中,亚当优雅的致辞被描述为“一套将连贯性和封闭感得以放大的电路”),那么这种源自精心构建的艺术性的令人振奋的感觉就与贯穿整本小说中对失控的胡言乱语的沉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是那些嘈杂的、说教的人,或是那些针对托皮卡的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以及亚当和他的年轻朋友们在聚会时沉迷的“某种混合在一起的男性胡言乱语”。或亚当的“后话语”祖父在其疗养院中逐渐陷入痴呆症的过程。对不稳定的语言的焦虑无处不在。乔纳森的早期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论”而进行,即当思想不堪重负时,“言语机制就会崩溃”。当简遇到往日的创伤时,“我的言语开始破裂……胡说八道变得似乎是合情合理”(此处让人想起《等待戈多》中幸运儿的话)。当女友抛弃他时(“从某个角度来说,就像他在无意义地饶舌”),或者他小时候头脑遭到重击时(“你的言语完全混乱”),亚当的辩词也是如此。《托皮卡学校》与乔纳森所描述的“在(语言的)‘悦耳的声音规则’之下无意义的河流”共鸣。
针对这一点,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那又如何?有哪个戴眼镜的布鲁克林小说家不对语言的不稳定性痴迷不已?但是,勒纳不仅仅是提供了某种令人疲倦的后现代主义叙述,耸耸肩去拥抱接受无意义的这一切。因为对无意义的担忧、对伪装成理性的非理性的忧虑,对于这本书的政治立场和艺术目的都是至关重要的:非理性与暴力相关,恶语引向恶行。需要再度提及的是,辩论比赛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隐喻。亚当可能是个熟练的辩论者,但他的论点在功能上毫无意义,纯粹是为了压制对手而提出的。简可能会“幻想他的能言善辩最终能被用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工作”,但此刻他只是在空洞地辩论,“一个模仿政治和政策语言的男孩”。(让简感到特别不安的是,在辩论中有一方说到“提到在可理解性的最极端时,这实际上是关于包容性”。)真正的问题是,在当代美国,“那里没有成年人”。乔纳森的导师,一个名叫克劳斯的德国犹太移民,以此诊断了该国的状况:“美国是无止境的青春期。”这个诊断是1970年代做出的,但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现在的方向。
在“文学枢纽”(Literary Hub)网站上的一次与诗人欧西安·沃恩的采访中,勒纳表示《托皮卡学校》是一部“关于家庭模式如何在几代人中重建或破裂,关于在九十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终结"话语如何掩盖了某些白人中加速恶化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史前史”。在亚当还是个小男孩时,与他母亲玩游戏的时候,他故意念错了一段简单的童谣(“再一次地,她用嘲讽的语气模仿,并以形式化的方式再把这段童谣背诵了一遍”)——亚当成年后,将这种游戏描述为“在几代人中流传的一种仪式性的对重复的拒绝”。在亚当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他的男性身份危机,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和诗人来面对生活本身的重担和口舌之争时,这种拒绝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里暗含着一个笑点,作者拿自己来开玩笑。将这个职业称作“重要的社会工作”)。但是那条非理性的、满溢着暴力的河流,仍然在地下轰鸣。在小说的最后部分,由亚当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带着两个女儿去游乐场。一个男孩占着滑梯与他们发生了争执(“又傻又丑的女孩不准上来”)。男孩的父亲很冷漠,看上去甚至似乎很喜欢这种情况,拒绝打破那种轮回(“男孩将是男孩”)。而当言语不奏效时,亚当以暴力回应。最令人烦恼的是,这一幕场景的设置却使读者感到满意。
迄今为止,《托皮卡学校》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尽管也有一些怨言。詹姆斯·马略特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他认识了一定程度的诚挚(“勒纳在为他的主题忧虑”),而在“文学枢纽”网站,艾米丽·邓普尔则认为最后一节“附加在外”。她反对将《托皮卡学校》的主要故事与当前的美国时事相关联,反对将游乐场事件——是的,提到了特朗普和“抓住私处”——以及亚当后来参加了某次占领移民局的抗议活动(这本书结局时的场景)作为“某种类似于美德的信号……勒纳向我们保证他具备良好的政治立场”。《新共和》杂志上的鲁曼·阿拉姆的意见更为激烈。他不喜欢达伦——桌球暴力事件的主角;被同辈世人疏远的老光棍——后来戴着一顶“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帽子重新登场,而且他觉得政治分析令人困惑。“我无法回答为什么本·勒纳一定要提到特朗普。也许这是对意义的追求,想要证明自传体小说也可以进行社会批判。”在我看来,这些反对意见似乎并无根据。勒纳将他的书形容为一部史前史是正确的,而最后这一段就是这样总结的。引用勒纳本人在评论克瑙斯高作品时候的说法,它提供的“结尾是形式之完成,并在回顾中组织作品的时刻”。读完它,我们就会意识到这就是这本小说一直以来营造的东西。社会批评不只是书本上的附加物,而是本书的核心:从开始时的湖上风景到亚当的成长岁月,再到贯穿全书的达伦的经历,在这本书的一切中,这个特征都清晰可见。
有趣的是,对《托皮卡学校》的这些批评似乎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在马略特眼中的某种认真的态度(这种倾向只会沿着单一的政治倾向,从右派向左派移动),邓普尔和阿拉姆将其描述为某种粗鄙的行为,就像是在说自传体小说,乃至所有虚构文学,都不足以说明我们当前时代的严重性。(邓普尔:“用过于个人化的方式来处理如此重大的事物”;阿拉姆:“当下的政治令人困惑……我想知道是否有小说家能真正与之抗衡。”)我认为勒纳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他写了一部轻重得宜,智性灵动,富于娱乐性的小说,并且超越了挖掘自己的童年或探索成为作家的意义。他面对了美国的男性气质、群体认同和边缘化、政治信息传递和世代交替的问题,而且他并无说教,而是大方面对,兼顾令人钦佩的敏感性。勒纳将《托皮卡学校》描述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并可能是文学上的一部告别之作:“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但是,鉴于它所展示的事实,他似乎并未耗尽自己的创造力。我们只能希望,这是另一种虚构。
(本文英文原文刊登于2019年11月22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获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上一篇:5个大好消息!
下一篇:一本不正经的男士说明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