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尔曼在他的专著《隐藏的成人: 定义儿童文学》中围绕儿童文学中固有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对立探讨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性。儿童文学的作者叙述者是成人,负责为孩子们出版、宣传和购买书籍的也是成人。正是这些“隐藏的成人”,既在创作时用简单纯真的文本寄托更为复杂的理念,也永远会是每个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后的第一批读者。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其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埃米尔擒贼记》《会飞的教室》《两个小洛特》等。
被誉为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对自己作品的双重受众非常清楚,也没有要将成人的影响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隐藏起来的意思,甚至公开主张作家应该同时为这两种读者写作。1953年,在苏黎世市政厅发表的演讲《青少年、文学和青少年文学》中,凯斯特纳声称,当时大多数普通儿童读物缺乏文学性,“那些只为小孩写书的作家并不是真正的作家”, 并由此鼓励************作家考虑开始为儿童写书。
既为成人也为儿童写作的凯斯特纳以身作则,在为儿童写的书中巧妙地结合了************中常用的现代叙事技巧——上一篇推送中介绍到,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处女作《埃米尔擒贼记》是第一个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所创作的儿童小说,本次的文章则会探讨凯斯特纳的另外两本书《会飞的教室》和《两个小洛特》中,复杂且有意思的叙述者形象及其对于儿童和成人读者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本文也是“儿童文学通识课”专栏的最后一篇。
儿童眼中的真实,
成人眼中的虚构
在《会飞的教室》一书中,叙述者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很突出:从“前言”开始的两章都是叙述者的独白,他也自称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在了解故事中的任何人物之前,读者首先被介绍给叙述者/作者本人,他有一个相当生动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写作时拖拖拉拉,喜欢为自己找借口(就如我本人……);他常常心不在焉,会丢失对他写作非常重要的绿色铅笔;他喜欢大自然,与他的动物朋友交谈;以及,他非常依赖他母亲对他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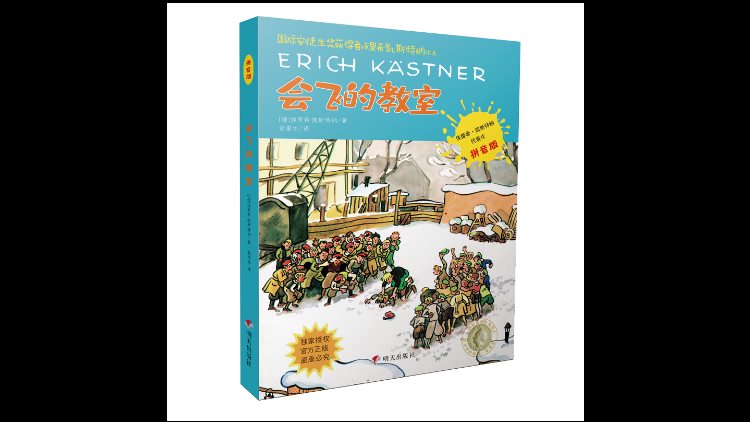
《会飞的教室》,[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赵燮生 译,明天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虽然叙述者显然是个成年人,但他选择在自己身上突出这些比较幼稚的特点,形成了一种幽默的矛盾感,并由此拉近与儿童读者的距离。同时,他通过描述他在楚格峰(德国最高峰)下写稿子的日常生活琐事,来试图说服小读者要相信他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全书的第一行话正是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 Christmas story.(这将是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
这种融合虚构和现实的方法在故事的“后记”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叙述者声称回到了他在柏林的公寓,一个比楚格峰更现实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他还讲述了他与故事中的两个人物,约纳唐·特洛茨(Jonathan Trotz)与他的养父的相遇。因此,凯斯特纳在故事中扮演了三重角色:他既是作者,又是叙述者,还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在与约纳唐的对话中,叙述者向他承认,他了解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他们在寄宿学校的生活,并且刚刚写了一本书,关于他们“两年前”圣诞节的经历——小读者在此时会意识到,这正是自己手中的书!这样,凯斯特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具有当代背景、连贯的时间线和可信的人物的“现实”,令儿童读者们信以为真。
然而,面对对虚构和现实的区分更加明确的成年读者,凯斯特纳这样的叙事手段自然就不奏效了。在“前言”中,凯斯特纳提问道:“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寄宿学校吗?”并对寄宿学校进行了一些介绍。对于小读者来说,这段介绍提供了关于故事背景的基本知识,并加强他们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信念。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故事中的设定最值得注意的是寄宿学校的“与世隔绝”。尽管故事发生在一个当代背景,这个“孩子们只有在假期才回家”的小镇上的寄宿学校,实则象征着与社会现实的脱离。与凯斯特纳同时代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和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笔下,寄宿学校是充斥着虐待狂的儿童惩戒所——不幸的是,这种刻画往往更贴近现实。
因此,正如德国研究学者斯普林格曼(Springman)所注意到的,凯斯特纳通过对寄宿学校的描写构建了一个 “另类的现实”,一个仍然崇尚着优秀的品质和友谊的世界。尽管故事中的男孩并不完美,而且确实会有一些不良行为,比如打闹之间施行的身体暴力(扇巴掌),进行危险举动(乌利打着伞从梯子上跳下来),以及霸凌(六年级的大孩子对低年级生的欺负),但这些行为都被视为可以纠正的。总的来说,个人的意志、友谊的凝聚力以及团结的群体,是建造这所寄宿学校的世界的基石。在这里,无论发生何事,正义总能降临。
《会飞的教室》一书出版于1934年,同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德国人民一定在许多方面深刻地体验到了生活的变化,但读者在故事中却找不到反映社会环境的线索。虽说凯斯特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任何幻想(fantasy)元素,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对其读者——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来说——仍是一种逃避的幻想,在黑暗的时代中描绘着那个更美好的平行宇宙。
因此,考虑到凯斯特纳本人对成年读者的知情,我认为他通过对“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这一故事设定的强调,在有意敦促成年读者考虑虚构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凯斯特纳仿佛在外部世界和他的虚构世界之间创造了道德上的两极,一头是世事无常的社会,一头是“真理”永恒存在之地。在这样的张力之下,儿童读者被鼓励全心全意地相信虚构的故事,相反,成年人则被邀请对现实进行反思。可以说,尽管凯斯特纳的作品并不反映当代的社会背景,但这本书仍可以被解读为他对道德崩坏的社会,特别是对1934年德国反人道的政权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所进行的回应。
“支起”世界的四种价值
在“前言”中,叙述者也扮演了道德家的角色,通过介绍约纳唐这一角色,向读者讲了长长的几段话,这似乎也与凯斯特纳大部分作品轻说教的风格背道而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凯斯特纳从未试图让他的作品不具教育性。他认为向小读者展示重要的价值观,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并声称 “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世界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在凯斯特纳的文章《四个阿基米德支点》中,他详细地阐释了他认为最重要的、有能力“支起”世界的四种价值,即:良知、榜样、对童年的记忆和幽默。这些价值也贯穿在他的各篇作品中。

根据《会飞的教室》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他的价值观隐藏在对代表这些品质的主人公的描写中,因为他深知儿童读者在接受道德教育时很容易感到厌烦。这一次,叙述者却在读者还没有见到主人公之前,就把这些观点直接灌输到读者的头脑中——似乎叙述者给予的这种训导是来自凯斯特纳本人的紧急呼吁。他试图 “支起”一个对这些价值观失去信心的社会,讲话所针对的对象也更多的是成年读者而不是儿童。叙事者说道“只有当勇敢的人变得聪明,聪明的人变得勇敢时,我们才能真正确认一些我们总是错误地笃定正在发生的事:人类在进步”,毫无悬念地影射着正在大倒车的德国社会。(在我看到的一些国内引进版本中,“前言”和“后记”甚至被直接删除了,或许是不理解它们的存在意义。的确,如果删掉它们,《会飞的教室》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随着故事在之后的章节的展开,人们不仅会遇到可以被视为榜样的儿童,而且还会遇到一对正直的成年人,他们也在年轻人面前重拾起童年的友谊。正如《埃米尔擒贼记》一样,《会飞的教室》中的主要人物们正是通过友谊的互助,深刻体会并展示了凯斯特纳笔下的美好社会所依赖的那些优良品质和准则。
凯斯特纳拥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友谊概念,认为它是 “在两个相似的灵魂之间发展的最崇高的关系,它们相互表达了良好的意图,不是出于对短暂的愉悦或利益的渴望,而是完全出于同类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友谊的种子“更常诞生于年轻的激情,而不是成熟的理性”。因此,通过两个曾为儿时故友成人角色的重逢,凯斯特纳将整个故事推向高潮,并由此恳请读者铭记童年的经历——叙述者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借此机会衷心地请求你,永远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童年”。凯斯特纳不仅想为他的儿童读者展示那些值得信赖的价值,而且还努力使友谊的纽带在成人的世界中保持活力。
向成年读者传递一些教诲
1949年出版《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 直译为“The Double Lottie”,但现在英译名基本上会采用由故事改编的电影所采用的名字The Parent Trap)时,战争已经结束,凯斯特纳似乎将他的关注点从社会价值转向私领域,着眼于家庭幸福,这也可能是他用女孩作为主人公的原因。友谊的价值被姐妹情谊所取代,这或许因为凯斯特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友谊概念的时代局限性就在于,它只被认为存在于两个平等的男性之间……

《两个小洛特》,[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赵燮生 译,明天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然而,当叙述者在故事开始时问读者:“你知道塞波尔(Seebühl)吗?”并随机介绍女孩子们参加的夏令营时,他又开始承担起了凯斯特纳笔下叙述者的重要工作,即构建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脱离的儿童天堂。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甚至自己指出:“难道只有那些我没问到的人才知道波尔湖畔的塞波尔是个村庄吗?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感到奇怪的,因为这种事是常有的。”这种轻松和俏皮的语气也贯穿全书。与《会飞的教室》中的叙述者不同,虽然在上一本书里,叙事者在“前言”中占据了读者的注意力,并在“后记”中把自己塑造成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但并未活跃在真正的故事情节中,而《两个小洛特》中的叙述者则一直闯入故事的讲述中。(如果句子结尾有像这样在括号里的话,那就是叙述者说的。)
叙述者的“碎碎念”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起到了几个作用。它增加了叙事的幽默和讽刺风格(“嗯,苍蝇是愚蠢的,但人类是聪明的……不是吗?”);它通过直接向读者提出问题,将读者也纳入叙事的一部分,使叙事具有一种轻松和对话般的语气(“他的语气是不是很感人?”);同时,它揭示了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动(“有一天他发现他在想事情,这个想法让他很吃惊!”);但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向成年读者传达了一些教诲。在解释两个小洛特的父母离婚的原因时,叙述者指出了成年读者的存在——虽然采用了一种针对孩子们的语气,“如果这时一个成年人碰巧在偷看你的书”。然后,叙述者利用这个借口,基本上算是给成年读者上了一堂课,告诉他们在处理有关婚姻的问题时要为孩子们考虑,要有开放的心态,因为成年人的选择也会大大影响孩子们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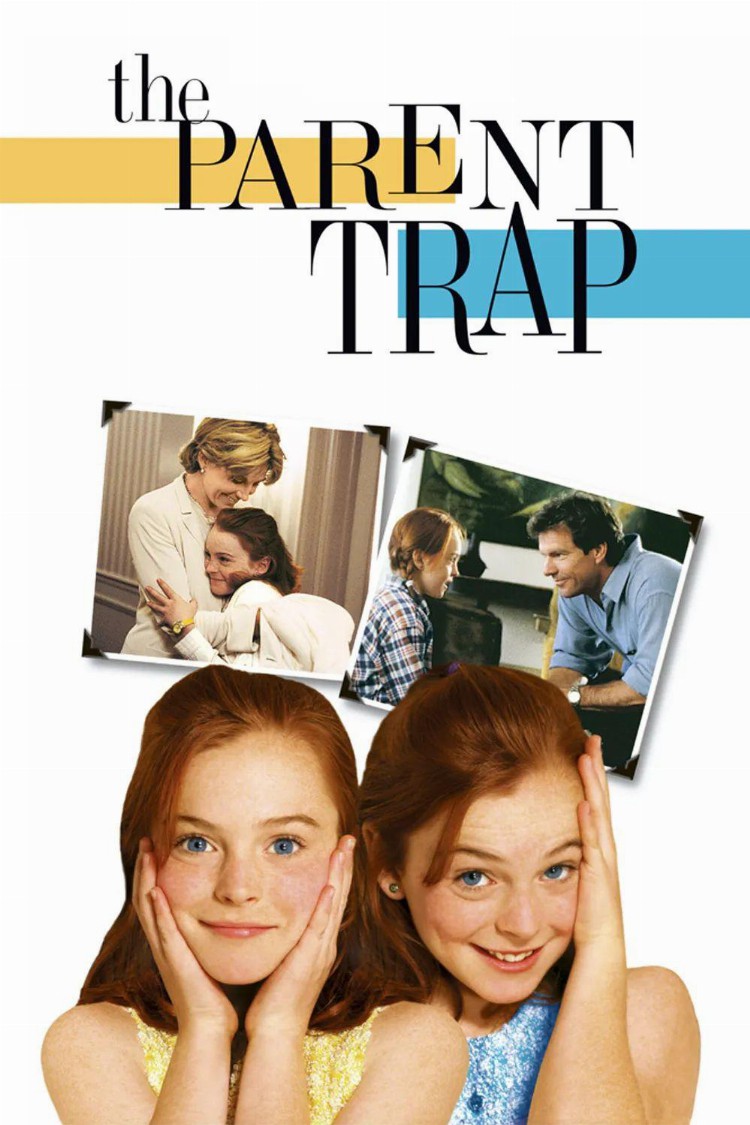
根据《两个小洛特》改编的电影《天生一对》(1998)海报。
总而言之,在《两个小洛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故技重施的凯斯特纳,通过叙述者强调不够现实的设定,并保持了向成年读者进行说教的作风,甚至开始以最直接的方式向成年读者讲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在阅读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时考虑孩子与成人这两类受众的重要性。
在儿童读物中采用更复杂的叙事策略的凯斯特纳,通过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不断传达着他的理念。正如用《会飞的教室》和《两个小洛特》的例子所讨论的那样,他书中的叙述者对他的双重读者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凯斯特纳在他的故事中为当时的小读者们提供了一个能产生联系的当下的时代环境,避免浮于表面的道德说教,从而鼓励小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把优秀的主人公们作为榜样。
然而,叙述者有意将故事中那些有着不现实因素的线索留给成年读者,敦促他们反思现实中存在的社会和家庭问题。正如儿童文学学者桑德拉·贝克特(Beckett)所说的那样,“被视为经典的儿童作品不仅对儿童有吸引力,同时还保有一层深意,让已成熟的感性也获得满足”。吸引着一代代儿童和成人读者的凯斯特纳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优秀且有开拓性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经典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电影《天生一对》(1998)剧照。
参考资料:
1. Beckett, Sandra L.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Writing for a Dual Audience of Children and Adults. Routledge, 2013.
2. Kästner, Erich. The Flying Classroom. Pushkin Children’s Books, 2014.
3. The Parent Trap. Pushkin Children’s Books, 2014.
4. Springman, Luke. “A ‘Better Reality’: The Enlightenment Legacy in Erich Kästner’s: Novels for Young People.”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4, 1991, pp. 518–30.
5. Weldy, Lance. Crossing Textual Boundaries i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作者/子葭
编辑/申婵 王青
校对/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