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往来的人形形色色,在老板眼中,他们既是读者,也是照顾生意的“衣食父母”。去年疫情期间,苏格兰最大二手书店的老板肖恩·白塞尔因过于想念曾经遇到过的顾客,而将他们写进了书中。
在这本《书店的七种人》中,肖恩戏称借用生物分类法上的林奈系统,将这些读者分成七类,有喋喋不休的文学教授、高调凡尔赛的行业专家、拖家带口的年轻夫妇,还有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等。他既吐槽一些读者的可恶可恨之处,更怀念书与人、人与人相逢此处的奇遇故事。
这些故事汇集起来,为我们勾勒了书店的生活百态,就像肖恩自己说的那样,他虽极尽吐槽之力,无非是想“像想念杳无音信的旧友一样想念他们。无论是迷人而有趣的人,还是粗鲁或无礼之徒,每个人我都无比想念”。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书店里的七种人》的第一章“属:Peritus(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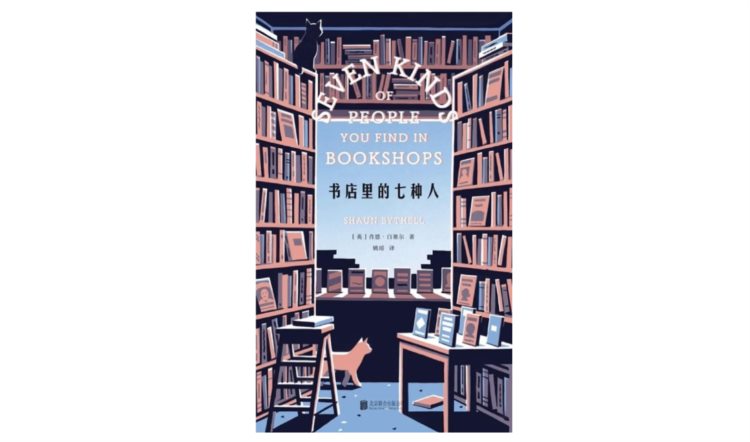
《书店里的七种人》,[英]肖恩·白塞尔著,姚瑶译,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
Peritus,如果你的拉丁语和我一样糟糕,那么你猜测这个词是指阴间某个讨人厌的地方完全情有可原。但它并非此意。它的意思是“专家”。
总的来说,这类顾客自诩专家,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听众来展现他或她的聪明才智。他们与大多数大学教师或公认的行业评论员不同,后者给出的观点通常都基于事实,且博学多闻,有学生和读者等着聆听他们的讲话内容。而接下来要讲的专家呢,绝大多数自学成才,他们可没有那样如饥似渴的听众。但一如往常,万事必有例外,在这类人里可以数出一些最最体贴的顾客,我能遇到他们真是三生有幸。而剩下的,真是让人讨厌得泪流满面。
专家们最热衷的莫过于使用超级复杂的词汇,明明短小精干的语言就已足够。集邮变成了“邮票研究”(philately),观鸟变成了“鸟类学”(ornithology),对昆虫的病态痴迷变成了“昆虫学”(entomology)。这就像是他们外出就餐,吃下威尔·塞尔夫作为主菜,然后咽下乔纳森·米德斯和斯蒂芬·弗莱作为甜品。不同之处是,塞尔夫、米德斯和弗莱全都已经吞下、消化并搞懂了整本《牛津词典》,并准确地知道如何在恰当场合使用正确词汇,让自己的散文文辞清晰。而专家们呢,则痛不欲生地让不情不愿的听众陷入混乱,别无任何惊艳之处。他们所知甚少,顶多五个高深词汇,却大用特用,说什么都用。结果呢,唯一的作用就是一举刮破他们智力优越感的浮面虚饰。但是我的药剂师朋友克罗达会这样说长单词迷恋症并非是嘲笑他人的理由,你有些人不知道化学品聚乙烯吡咯烷酮是大多数处方药片中所含有的一种结合剂就去嘲笑他们。
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就语言的使用有过赫赫有名的争论,福克纳讥讽说“谁也没听说过海明威用过一个需要让读者去词典里查一查的词”。对此,海明威的回应则是“平庸的福克纳。他真的以为崇高的感情来自复杂词汇吗?我和他一样了解那些艰深词汇,但我更喜欢那些古老、朴素的单词们”。就海明威对“们”的用法,我在学校里的英文老师恐怕会高度赞同福克纳,他肯定会争执说,“单词”后面不应该加“们”,只能说“几个单词”,或者“很多单词”。同样,在对待“alternative”这个单词时,他也相当迂腐。他坚持这个单词的词根来源于拉丁语“alter”,指的是两者之一,所以不能有复数形式。因此在课堂上提出有两个甚至更多的“alternative”时,总是我们巨大的快乐源泉。
类型一种:doctus(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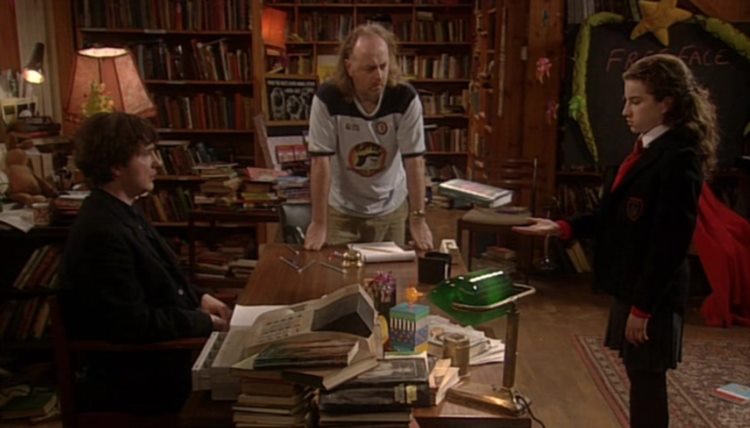
英剧《布莱克书店》(第三季)剧照。
这类人踏进书店没有别的理由,只是为了长篇大论地给你上课,告诉你他们的专业兴趣是什么。若你对这一领域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就能得到独特的快感—因为你几乎肯定是不了解的。大部分经营专业类书籍的书商都通过多年的积累,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这悉数反映在了他们的藏书上。可是,若你经营一家大众书店(像我这样),就不可能无所不知。尽管如此,对那些将自己成年后的人生都奉献给了研究西伯利亚树栖蜗牛繁殖习惯的人,你坦白这点试试。当你透露出,不,你不曾听说过米哈尔·霍萨克在这一课题上影响深远的研究《古生态重建中的软体动物群落:利用传递函数模型对其预测能力进行研究》时,他们定会以一副傲慢的神情讥讽你,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喜悦与轻蔑(两者程度相当)。虽然这些人会从你对其专业领域的无知中获得快乐,但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你或者其他人不想花二十年时间蜗居在鄂木斯克五十英里外树林的帐篷里,带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架检测蜗牛粪便的显微镜,除了与这一科目相关的晦涩学术论文以外,什么都不读。
在这类人中,极少数更擅长社交的成员则意识到,其他人或许无法分享他们难以理解的兴趣。于是,这一小撮人从另一件事情上获得了替代的快感,那就是他们对生态位的迷恋。这项爱好多少有些与众不同,而这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看上去更有趣了。我们曾经有位常客,总能成功地吓人一跳。他悄无声息地进到店里来,突然出现在柜台旁,爽朗地同我们打招呼以宣布自己的存在,“你好啊!我这人有点古怪,我,我超爱阅读有关不同结石之间区别的书。”但叫人痛苦的赤裸真相是,事实上,他对不同结石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没兴趣,只是因为自己太过乏善可陈,因此觉得告诉别人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就能够拓宽自己的人设。然而并没有。不言而喻,任何自称“有点古怪”的人,显然都不怎么古怪。
类型二种:homo odiosus(讨厌的人)

电影《书店》剧照。
这类人总觉得自己是个博学家,一旦你注意到他们的癖好,就会发现,在任何你选择提及或偶然提及的话题上,他们都要积极同你分享自己的想法。他们在场时你最好保持绝对沉默,因为就连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触发其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讲的还是你最反感的话题。不过,你往往很难发现客人们竟然属于这一分类范畴,直到一切为时晚矣。他们毫不避讳地去听别的客人谈话,然后用自己的观点横加打断(通常充满攻击性)。在诸多场合,我都不得不同无辜的旁观者道歉。他们原本只是在小声交流,结果却遭到陌生人的一通咆哮,这个陌生人恰好能听到他们说话,未经允许便擅自开口(很有可能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在这类人中我们有一位杰出的代表,接下来的几段记述了我朋友某天来店帮忙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充分说明不知如何与这类人打交道的危险。
一个夏天的星期六早上,天气温暖,我的朋友罗宾十一点钟出现在店里,在书店靠前的柜台后面驻扎了下来。我当时正在店里四处转悠,假装工作。一如往常,书店的日常生活就是你来我往,数小时之后,附近著名的讨厌鬼阿尔弗雷德拿着三本书去了柜台。他带着一种平静的、沾沾自喜的神情,将书重重地放在了木质台面上,眼睛则死死盯着罗宾,仿佛是在提前宣布这些书“很重要,因为正是它们造成了目前这种情况”。
在被阿尔弗雷德折磨了二十多年后,我深知,面对他可能抛出的一切引导性言论,唯一安全的回应就是沉默。不幸的是,我还没有机会教导罗宾如何应对这类情况。除了在阿尔弗雷德背后手忙脚乱地朝他打信号、让他别吭声外,我什么也做不了。好在老天保佑,阿尔弗雷德问能否把书先放在柜台上,他要去银行的ATM机上取点现金。
等他走远到听不见我们说话时,我马上提醒罗宾,阿尔弗雷德明显就是等着我们当中有人开口向他提问,所以千万别问问题,以免承受那没完没了又自以为是的演讲。他要说的就那点东西。“等他回来付钱的时候,千万别说任何可能被他误解的话,让他以为你对他不吐不快的那些事儿感兴趣。”这是跟罗宾分开前我叮嘱他的话,随后我就上楼去煮茶了。坦白说,我的话毫无说服力,我也不幻想自己做的这些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
二十分钟后,我人在厨房里,此时疲于应战的罗宾出现了。他解释说,我刚离开,阿尔弗雷德就回来了,但是没能从ATM机取到现金,因此避免提及任何可能让其误会罗宾对他或他的书感兴趣的话罗宾建议他使用免接触式银行卡付款。“结果这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我不得不听上一段有关网络安全的长篇大论,内容偏执多疑。我真心觉得他永远也说不完。”
我尚未发现阿尔弗雷德对哪个话题没有令人不快的深刻见解,也没发现阿尔弗雷德对哪个外国人不曾怀有毫无道理的恐惧。而意料之中的是,对自己这种毫无理由的仇外情绪,他的解决方式是希望国家重拳出击,其手段通常包括驱逐出境或监禁。而所谓的罪行呢,不过就是他们无法共享他的观点。
类型三种:homo utilis(有用之人)

电影《书店》剧照。
并非所有专家都惹人厌烦,当然了,除非你是迈克尔·戈夫。有时候,专家能够派上大用场。一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位住在邓弗里斯的女士的电话,她一直在清理自己的藏书,急需卖掉一些。那是个寒冷阴沉的下午,当我来到她位于足球场附近的独栋平房时,发现一箱箱的书堆得到处都是。这些藏书趣味十足且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上百本她丈夫收集的板球类的书;而她自己则收集毕翠克丝·波特、“观察者书系”和“瓢虫书系”之类的书籍。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书店里的优质库存。在翻检这些藏书的过程中,我拿起一本不太吸引人的平装书,是帕特丽夏·温沃斯的《荒凉之路》,就在此时她评论道:“哦,那真是本有意思的书,特别罕见,而且价值连城。”我看着这本书,封面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盒巧克力上放着一根针管。我是绝不会说这本书罕见或者价值连城的,然而她解释道:“桑顿的人,也就是巧克力公司的人,反对这一封面,因为他们认为,将他们的产品与注满毒药的针管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损害其品牌形象。所以这个封面就撤回了,化成了纸浆,然后他们又设计了另一版封面。”这类信息对一个(偶尔)需要说服人们相信自己不是在胡扯的书商来说,珍贵无比。
我有或者说直到不久前还有一位常客,名叫哈米什。在我还差几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去世了。他是个息影的演员,非常痴迷于军事历史。同他聊天是件赏心乐事,他肚子里从来都不缺好故事。他对二战课题很感兴趣,对这一领域的了解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专业科研人员,却从不厌倦,也从不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
在我们短暂的谈话当中,他会简明扼要地掺入一些极其迷人的内容,都是精心打磨过的,并且总是让我意犹未尽、想去了解更多。我会格外想念他。
类型四种:homo qui libros antiquos colligit
(古书收集者)

电影《书店》剧照。
古书收集者是一类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对书的兴趣往往在于将书作为一个物件,而不是其中承载的内容,尽管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许多对古书感兴趣的人都是用它们来进行学术或者家族史的研究。如何从自己的专攻领域之中甄别出特殊版本,对此古书收集者始终拥有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知识,深谙其道。比方说,罗伯特·彭斯著作的早期版本,尤其是《苏格兰方言诗集》。搜集这本书的人会翻遍书店的书架,寻觅极难找到的基尔马诺克版,那是由基尔马诺克人约翰·威尔森于1786年出版的版本。他们知道在六百一十二本的预订版中,只有八十四本留存了下来。而且这一版本很好辨认,因为彭斯将这本诗集献给了加文·汉密尔顿。他们也完全了解本书的二版二刷(1787年的爱丁堡版,献给“苏格兰皇家狩猎部的贵族与绅士”彭斯是个收税人员,很清楚怎么做才对自己有利)中多收录了十七首诗歌,《颂献哈吉斯》里还有一处印刷错误。这首诗里的苏格兰语单词“skinking”(意思是“水汪汪”)被错误地排成了“stinking”。这一错误在伦敦版里延续了下来(也是1787年出版),这些版本成了后来著名的“stinking版”。这种神秘的知识似乎有些强迫症意味,但那是因为对某个课题相当狂热的人往往都会有强迫症的特质。
专家属中的古书收集亚群的另一个特质便是不可避免地对价格报以不满的啧啧声。没错,那可能是十二卷一套的限量签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由亚瑟·拉克姆绘制插图,标价六百英镑。我可以向你打包票,那些羡慕地摩挲它的顾客绝对会不满地摇摇头,告诉你说他们在别处看到过这套书,要价要便宜得多。但若果真如此,那他们还如此贪婪地盯着你的书未免也太奇葩了。啧啧地告诉书商你见过更便宜的版本,这样是不太可能获得折扣的。我们都很清楚有时买书会多花冤枉钱,或者某些书的价格会有所下降,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抱怨说看到其他书店卖得更便宜,就给一本书降价而自己承担损失。
我有位买古书的常客,尽管他到柜台来的时候,账单常常达到三位数,但他总是能做到在离开书店的那一刻,让你感觉仿佛被打劫了一般。他已经退休,显然家境富裕,对稀有图书抱有兼容并蓄的兴趣。上一次他来店里的那天早上,我刚从一位极其有趣的老人那里买来一堆藏书。老人一家显然已经两只脚都踩在了更高的社会阶层上。这些书曾舒舒服服地躺在一个豪门的书架上书上有你在收藏古书时总盼望见到的图书馆馆戳;纹章历史悠久,纸张间弥留着用人添火时的木头味儿。但是,显而易见,这个家庭后来家道中落,房子也没有了。我怀疑这是藏书室里最后的零头了,它们被装在超市的面包箱里带过来。我无法确切记清付了他多少钱,不过我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因为还有些书我当时没空进行检查和评估,如果最终定价过低,我希望能补偿他。我估摸着其中应该有一套马洛礼两卷本的《亚瑟王之死》,由奥布里·比亚兹莱插图并题刻。那个古书收藏家来到店里,仔细翻检了我刚收来的货物,最终,一不小心发现了比亚兹莱的那套书。他问我要价多少,在根本还没机会做详细研究的情况下,我告诉他八百英镑,结果他(出乎意料地)开心地付了钱。几个月后,在卡莱尔图书节上我偶然遇见了他,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在伦敦拍卖会上,他将那套书卖出了一万九千英镑的高价。
作为一个书商,我感到,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卖书给我的人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觉得被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卖书给我的那位老先生。如果同样是由我来销售这些书,并且也卖了一万九千英镑,为了让自己心安,我一定会给他写张支票,把大部分收入都归他所有。没错,;我们都爱便宜货,但在这类事情上,钱并非全部。没人会乐意觉得自己上当了。这位古书收藏家很清楚我没有机会发现这套书的更高价值。如果他愿意同卖书给我的那个人分享这一万九千英镑,但把我踢出局,那我简直能高兴死。
尽管有这样的遭遇,但古书收藏家似乎是个濒危物种,这一现实还是令我感到难过。“濒危物种”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绝大多数藏书人。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数量一年少似一年。知识不再仅是书籍贮藏的内容,严格说来,书籍或许不再像曾经那样作为知识的源头而那么珍贵了。我父母的朋友布赖恩收集杰弗里·法诺尔的书,由于这个作家实在是太过时了,所以几年前我就不再收购他的书。我已经在诸多场合告诉过布赖恩这件事,可他完全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人在苏格兰,就一定会到店里来,问我有没有新收来的法诺尔的书。他有张清单,写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里,并且他总是带着一股我始终无法拥有的乐观激情破门而入。我这儿从来没有他在找的东西,主要原因是我已经将所有法诺尔的书都送去废品回收了。想到这会导致将来的某一天布赖恩最终不再到店里来,我感到有些心痛。我怀疑,直到我最后一次关上书店的门,是否还会有人再向我问起杰弗里·法诺尔的作品,除非他能享受到始料未及的翻红,就像温斯顿·格雷汉姆的《波达克》系列小说那样。在BBC拍摄了这个系列之后,演员艾丹·特纳在每一集里都要脱好几次上衣,也因此让这个系列出了名。
类型五种:mechanicus in domo sua
(家庭机械师)

电影《书店》剧照。
这些顾客是绝对的快乐源泉。通常,他们都是为路虎寻找《海恩斯手册》。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也从不失望;但若你恰好有一本,那他们则会喜出望外。除了与汽车相关的书籍外,他们什么书也不看。可是,谁又在乎呢?他们就读他们想读的东西,像每个人一样,没有一丁点儿在文学上的自命不凡。我喜欢并且尊敬他们。他们激情满满、令人愉快,值得最高的赞赏。他们会津津有味地吞下自己的文学猎物,比在牛津大学研究乔叟早期手稿的教授找到一本早期的卡克斯顿版古书还要热忱。这种快乐是他们应得的。他们渴望信息,无论这信息是1947年的萨福克矮脚马牌割草机的火花塞直径大小,还是1976年的福特科蒂纳齿轮箱规格,都无所谓。活字印刷本该为这样的人发明出来才对为这些使用书面文字真真正正做实事的人,而非那些装模做样的人。那些人搞得好像活字印刷之所以存在,要么是为了推动他们特定的宗教偏见,要么是为了印证他们对水占卜或梦境解析这类伪智慧的信仰;抑或是为了使其自我催眠自己在斯劳的小屋位于六条地脉的交汇处,因此应当具有国家级名胜的地位。但事实上,它真正的归属,应该是在一群推土机的轮下。
家庭机械师总是紧张兮兮地走进书店,常常穿着油腻腻的工装裤。当你告诉他们,你确实收有老旧的《海恩斯手册》时,他们便满心欢喜。即便你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总能找出一本来,而且还恰好与他某个朋友正在修理的车子相关。我住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在购买老旧汽车进行维修。他就曾提到《海恩斯手册》,说是“海恩斯的谎言之书”,因为总有一些线路,或者制动液储液罐,与他当时在修理的汽车的真实状况不相匹配。
*
就Peritus或者说专家属而言,总的来讲,类型一和类型二是你绝对想从书店里一脚踢出去的那种人。通常情况下,类型一就知道在那儿自吹自擂。这些人的丈夫或妻子终将非常腻烦他们多年来的相伴,可以做到完全无视他们。而书店则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完美场所,让他们能够夸夸其谈。对类型二而言,政治是其相当热衷的主题。他们通常毫不在乎“受害者们”可能不同意其观点这回事儿,无论这观点有多么极端。气候变化(他们通常否认)、同性婚姻(他们通常反对),还有欧盟(我们就别讨论了)都是他们的惯常话题。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越是无动于衷,他们就越是觉得有必要更大声地叫喊出来。类型三和类型五成为了越来越稀缺的类型,这样的人你会想同他们共进晚餐。而类型四则成了欠你好几顿晚餐和一瓶昂贵葡萄酒的家伙,但无论是美食还是美酒,你哪个都别想看见。
本文内容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书店的七种人》一书,内容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 | [英]肖恩·白塞尔;
摘编|青青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