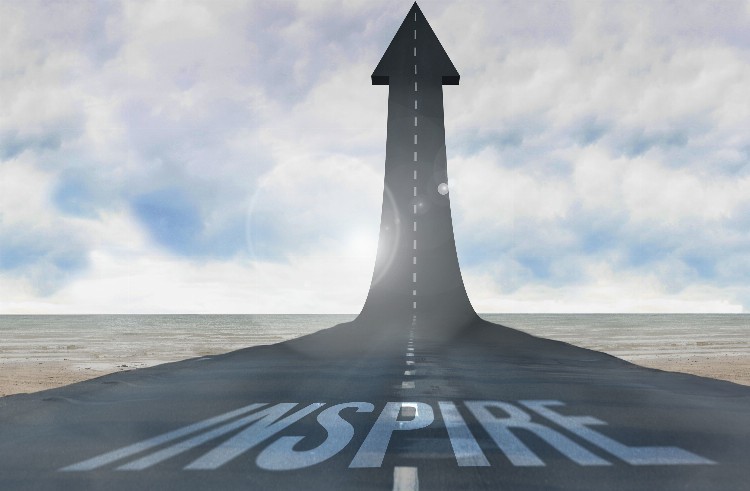
07 博学的重要性
|米特拉的实验|
1999年,苏加塔·米特拉(Sugata Mitra)在新德里的一所学院向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讲授计算机编程课程。学院旁边就是一个贫民窟,他可以在办公室里看到其全貌。从窗户向外望去,他会不时地思考:在这如此拥挤的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们,是否有机会使用电脑?如果是,他们又会用电脑做些什么呢?
下课后,米特拉的那些富裕阶层的学生们会讲起他们孩子的事情,夸耀自己成绩优异的子女是如何使用昂贵的计算机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这给米特拉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让他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可能只有这些有钱人才会有天赋异禀的后代呢?”
这个问题令他进行了一场即兴实验。米特拉在贫民窟的围墙上挖了一个洞,将一台事先连好网的电脑的显示器和鼠标固定在洞中离地大约一米二的地方。贫民窟里的孩子们慢慢聚集过来,睁大眼睛问:“这是什么?”米特拉耸了耸肩假装不知道,然后走开了。
八个小时以后,米特拉回到了实验地点。它发现孩子们正围在电脑周围熟练地上网。这一幕让他惊呆了。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没有见过电脑,他们是如何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学会了使用互联网的方法呢?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事们,其中一位同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可能刚好有一位老师经过,并且教会了孩子们怎样使用鼠标。米特拉心存怀疑,但还是勉强承认这是一种可能性。之后他在距离新德里五百公里处的一个村庄重复了这个实验。那里是印度偏远的农村地区,一位软件工程师碰巧经过的概率非常低。
知识与理解的关系,就如同光与眼的关系;孩子们对它充满热爱,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发现,以及我们是如何鼓励和表扬他们的求知欲的时候。
约翰•洛克(John Locke)
当米特拉两个月后回到村里时,发现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用电脑玩游戏。“我们想要一个更快的处理器,”孩子们跟他说,“和一个更好的鼠标。”当米特拉问起他们是如何学会使用电脑的,他们气鼓鼓地解释说,因为米特拉给他们装的电脑只有英文系统,所以他们只好先自学了英语才能来使用它。
米特拉在印度农村的不同地区多次重复了这个实验,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其中一个实验地的儿童们学习使用“洞中电脑”的过程。录像显示,他们互相教授使用方法,朋友教会朋友,弟弟教会姐姐。米特拉将自己的发现撰写成一系列的论文,并总结道:“将一台使用任何语言系统的电脑留给一群孩子,只需要九个月的时间,他们对电脑的使用就可以达到一名办公室秘书的标准。”
在这之后,米特拉萌生了一个更为大胆的问题:在南印度村落中生活的说塔米尔语的儿童们,能否通过一台放在街边的装有英文系统的电脑,学习到一些有较高认识要求的知识呢?米特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希望这个结果至少可以让雇用更多的教师成为可能。他选择了一个村庄,安装了一台电脑,并下载了有关DNA复制的资料,然后便把这台电脑留给了孩子们。两个月后他返回到村庄,对孩子们进行了测试,结果他们并没有及格。又过了两个月,孩子们告诉米特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进展。他并没有感到惊讶,直到一个小女孩举手并站起来,用塔米尔语和蹩脚的英语说:“我们除了知道DNA分子的非正常复制将导致疾病以外,其他什么都没学到。”
米特拉意识到虽然孩子们的分数没有及格,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确在进步。他决定为他们找一位辅导员,就请了一位在当地生活并熟悉这些孩子的年轻女会计来帮助他。会计告诉米特拉,她对DNA复制一无所知。米特拉建议她使用“外婆方法”——在孩子们玩电脑的时候站在他们身后,发出赞许的声音,并且问他们在做什么。
又过了两个月,孩子们的分数达到了50分。这些生活在泰米尔纳德邦贫穷村庄里的孩子们,达到了实验控制组的那些孩子的分数,也就是新德里私立学校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正是如米特拉编程课上的学生们那一类人。
米特拉现在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的教育技术教授。他相信南印度的孩子们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现在是时候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了。他说,我们的教育体系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一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需求。我们的学校善于制造高效的最终那一丝了,曙光降临。管理者来经营一个帝国,却不善于培养好奇的学习者。互联网已经使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传输知识的成年人)没有了用武之地。所有的学习都可以通过与泰米尔纳德邦的孩子们学习DNA复制知识时一样的途径,再加上宽带网络和来自朋友的一点帮助就行。
最终,那一丝曙光降临了。
查尔斯•达尔文
米特拉的研究在他的TED演讲之后变得广为人知(我的叙述即改编自他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提出互联网的出现急需一种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革新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技术预言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互联网的无限存储能力意味着我们将不再需要把所有事实和信息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学习不再是记忆各种知识,而是自由地去探索知识。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就是,“博学已经过时了”。
|好奇心驱动的教育|
学校是好奇心的熔炉,它既可以锻炼儿童用力量与筋骨去追寻初出的求知欲,也可以任凭其消散殆尽。如果你像我一样关注好奇心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你一定也听说过关于学校的目的和意义何在的长期争论。分歧之处在于:学校到底是一个成年人向儿童教授社会认为有用的知识的地方,还是一个任凭儿童随意追寻自己好奇心的地方?
米特拉教授提出的“技术推动教育改革”的观点可以从这一长期的争议中得到最好的体现。虽然“博学已经过时”的主张听起来具有激动人心的未来感,但其根源能够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一种被称为“好奇心驱动的教育”(curiositydriven education)的想法,即认为学生基本上不需要记忆成人传授的学术知识。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每一代人都会将它重新演化一遍。
米特拉没有提到过他的思想渊源,但是他的大部分论点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身上——18世纪末掀起的一场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让-雅克·卢梭。他在1762年的《爱弥尔:论教育》(Émile: Or, On Education)一书中,用一个虚构的、名叫爱弥尔的男孩来说明儿童可以不需要成人的干预就可以学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天生的好奇心就是儿童最好的老师。“让我们……尔略先前所学的知识,因为它们对我们没有天然的吸引力,转而关注于那些使用本能来推进的学习,”卢梭写道,“儿童不应该通过语言传授的课程学习,仅应该通过经验主义来学习。”
根据卢梭的观点,成年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太爱将自己非自然的、独断的知识强加给孩子。他问道:“在他们的大脑中刻上一串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符号究竟有什么意义?”学生们也许可以背诵那一串事实,但却没有理解。这些嵌入他们大脑的事实,迟缓而无用,只会破坏他们的思考能力。让学生学习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格格不入的信息,是对他们本性的一种侵害:
不,如果大自然给予了孩子大脑的可塑性,让他能够接收各种各样的印象,那么你就不应该在它上面刻上国王的名字和登基日期、纹章学的术语、地球和地理知识。所有那些字眼对孩子而言,在当下没有意义,在以后也没有用途,只会淹没他悲伤而贫瘠的童年。
卢梭是一位观点独到的思想家,也是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他提出的“儿童天生的好奇心会被成年人的教育方法所抹杀”的观点是经久不衰的社会迷因——一个能够不断再现的思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延续至今,爱弥儿的故事被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讲述。虽然版本、语言文字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最终都重现着同样的主题。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们创立了进步教育学校,其核心原则是教师不得介入儿童与生俱来的对探索和发现的热爱。传统的教学科目如历史、语文和算数被降低了比重,毕竟只有极少数的儿童对它们天生感的兴趣。教育的重点转变为“在工作中学习”,也就是动手实践而非口头传授。指令性的教育被禁止或者受到限制,转而鼓励儿童玩耍和自我表达。
玛丽亚·蒙台梭利学校(Maria Montessori School)是这种进步主义哲学最负盛名的例子,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都上过蒙台梭利学校,并且称赞蒙台梭利的精神气质对他们的成功有所帮助。20世纪70年代,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巴西教育家保罗·费列罗(Paulo Freire)曾批评那些填鸭式的教育,即向学生灌输与他们的存在经验无关的知识。他说,教育不是把学生当作储蓄知识的银行,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起自立能力。
进步主义的当代版本总是与学习能力(有时被称作高阶能力、思维能力或者最近也被称为“21世纪能力”)一词联系在一起。蒙台梭利与其同时代的人坚定地崇尚教育与学习这一过程本身,而学习能力的倡议者们则更关注于学校如何让学生适应将来工作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两者都认为,学校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来教授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知识,而应该专注于提升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如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好奇心。这些能力能够训练学生们应对未来所发生的任何困难。
这一哲学思想已经深入教育界的主流。每当你听到赞扬学生自己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性,或者批评教师花太多的时间授课而不是允许学生表达自我的时候,其背后都是这种思想的支撑。在英国某教育工会的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直接说明:“21世纪的教学大纲不能将传授知识当作核心内容。”
近几年来,学习能力目标被技术预言家们与火热的硅谷式创业和DIY精神联系起来。维基百科与谷歌的时代可能是卢梭梦寐以求的。任何一个拿着iPad的孩子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探索全世界的知识,而不需要老师的干预。教育咨询师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说:“孩子们不需要人帮助他们学习……他们生来就有对知识的贪婪的渴望……而一旦我们开始填鸭式教学,这种渴望就开始消散。”既然互联网让我们不再需要记忆事实,学校就完全可以关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这听上去像是个现代的想法,但与爱弥儿的思想如出一辙:工业化扮演着如敌人一样的角色(传统学校总是被冠以“工厂”之名),传统的教育方法也备受怀疑,人们夸赞儿童无拘无束的好奇心来强调个人体验的重要性。“21世纪能力”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所体现的教育思想最初出现在法国处于帝国时期,而美国处于被英国殖民时期。
学习能力的倡议者们通常不会承认他们的思想渊源。这虽然奇怪,但也情有可原。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他们的思想因为与现代科学对学习行为的认识相矛盾而被一次又一次证明是错误的,但总是被一再地重新提出,就好像每一次都是新鲜、闪亮,能爆发出无限可能性一样。我们现在知道卢梭是错误的,儿童好奇心的机制与他及其同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不同。他的想法很诱人,但是之所以会被不断地重新提出,是因为它并不起作用。
|对学习的三大常见误解|
为了理解背后的原因,让我们来讨论好奇心驱动教育的支持者们对学习的以下三个常见误解。
误解1:儿童不需要教师的指导
那些认为教育性的指导会抹杀儿童天生好奇心的人忽略了人类本性的一个基础——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向来依赖于我们的前辈和祖先所给予的知识。我们这一代人不需要重新发现如何使用火或者如何建起摩天大楼。每一位科学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每一位艺术家都属于或对立于某个传统。最近,婴儿向他周围的成人学习语言被发现与保罗·哈里斯所称的“古老的导师制度”有关系。
儿童依赖父母的时间比其他哺乳动物要长得多。这间接地证明了人类天生就应该从成人那里学习,而不是独自探索。无论在哪一种文化背景下,成年人都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尽管指导的方法和范围不尽相同。哈里斯引用了利比亚的一位格贝列人(Kpelle)父亲的话:“当我砍灌木的时候,就会给孩子一把砍刀,让他也学习如何砍灌木;如果工作变得太难,我会教他如何简化。”这种对下一代细致的教育方式融入了我们的遗传基因,与当代人对人类本性的曲解不同。反而是卢梭构想让爱弥儿在一个彻底隔离的环境中学习,才背离了人类的本性。
大量的经验性证据表明“无指导学习”一词是一种矛盾修辞。加州大学的认知科学家理查德·迈耶(Richard Mayer)调查了1950年至1980年间进行的研究,对比了无指导学习与传统方法的差异。在每一个案例中,儿童在成人指导这一旧方法中的表现都超过了实验性教学。迈耶强调,同样的思想换成不同的名字(发现式学习、经验式学习、构造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层出不穷,尽管每次都表现得不是那么有效。
当然,教师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什么和怎么学的直接指导,而且这还应该是他们工作的核心。研究者约翰·海蒂综合了超过800项关于成功的教学方法的分析。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三个最强有力的、最可能推动学生成功的教育方针是反馈、指导的质量和直接指导。换句话说,当传统教学(即成人向孩子传授知识)遇到一位好老师时,就是高度有效的。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当海蒂向接受教育培训的学员展示这一结果时,他们显得很震惊,因为他们通常被告知直接指导是一件坏事。
而且,当儿童缺乏成年人所传授的知识时,他们天生的好奇心其实并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Babylab的研究表明,认识性好奇是一种“做好学习准备”的状态。除非儿童的认识性好奇最终被知识的供给所满足,否则它将很快消退。如果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被给予直接指导,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气馁、迷惑,甚至相信错误的结论,从而危害到将来的学习过程。互联网对此也无能为力,反而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假设有一群学生想要学习达尔文进化论,但是手中只有一台连网的电脑,有多少学生会得出“进化论是撒旦的阴谋”这一结论呢?一些学生也许会学到一些宝贵的知识,但是途中会损失大量宝贵的时间要从虚假和无意义的信息中甄别出有根据的讨论。虽然培养儿童独立学习的能力是重要的目标,但是如果儿童被要求直接从独立学习开始,那他们不可能走得太远。
学校与教师同样应该告诉儿童要学习什么,以指导他们接触那些虽然他们自己暂时觉得乏味,但是家长和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意外之得”在人童年时期的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师们可以帮助学生偶然发现他们以前不知道自己会感兴趣的知识(即所谓的“未知的未知”)和那些最初接触时觉得枯燥或者困难的科目。如果你翻开《哈姆雷特》的第一页看到的只是通篇的胡言乱语,又如何会认为自己将热衷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个能够解读这些胡言乱语,并且说服学生应该坚持下来的老师,也许能够改变学生的一生。儿童需要得到一定的信息才能理解到自己的信息缺口,有时这需要非常明确的指导。否则,我们将会让他们由于无知而陷入到永远的冷漠之中。
当然,在某些学校和某些课堂上,缺乏想象力的老师可能没有努力让教学内容变得有意思而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这就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然而,因这部分老师的做法而得出所有的教学指导在原则上都是错误的,是一个在错误方向上的野蛮跳跃。文化延续的载体需要英明而熟练的掌舵人。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他们所出生的这个社会的掌舵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找到舵轮。
误解2:事实抹杀创造力
TED论坛将所有的演讲视频都免费放在网上,演讲者包括国家元首、摇滚明星、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亿万富翁。然而点击量最大的视频是一位和蔼的中年教育咨询家的演讲。他来自利物浦,在登上TED舞台之前,几乎无人知道他。
肯·罗宾逊爵士在2008年有关教育改革的演讲《学校是否抹杀了创造力》突破了400万的点击量。罗宾逊爵士在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项事实:随着儿童逐渐长大并在学校里的年级不断升高,其标准创造力测试的分数却在降低。他的结论是儿童天生就是好奇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而工厂式的学校反而让他们变得木讷。他们被灌输了太多的学术知识,而自我表达方面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提升。罗宾逊爵士显然深切地关注着儿童的幸福感,并且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对于创造力的论述引人入胜,然而却几乎完全没有根据。
创新始于跨界。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指出,“黄金”与“山”这两个概念本身平淡无奇,但是“黄金山”听上去就很有意思。罗宾逊等进步教育家批判已有知识是新思想的敌人。但是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我们所有的新想法都来自旧的想法:为了想象出一匹插着翅膀的马的图像,你必须首先熟悉翅膀和马的概念;为了发明智能手机,你首先要知道电脑和电话。知道的知识越多,这种新的跨界就越多,参照物和类比也就越多。事实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想法,可以找到很多方式对其加以应用。
我们将儿童的好奇心浪漫化是因为我们喜爱他们的无邪,然而创造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成功的发明家和艺术家会花很大的力气来积累大量的知识,这才使他们将来的创造变得轻而易举。在掌握了领域内规则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改写它们,不断地融合各种想法和主题,创造新的类比,发现不寻常的模式,直到实现创造性的突破。
研究创新的人们发现,科学家和发明家作出突破性进展的平均年龄段正在逐渐上升。由于知识在世代更替中慢慢积累,个体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掌握,相应地,达到能够更新和补充原有知识的层次也需要更久。[1]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在自己的领域中积累多年的知识才可能创作出杰作。典型的例子就是神童莫扎特在他开始音乐事业后的第十二年才写出了第一部传世之作。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这样说道:“天才都是书呆子。”没有了包括事实性知识在内的知识积累,一个孩子就像雕塑家没有了粘土——他虽然具有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却徒有其名。
下面是一些有关人的好奇心被事实性知识所填补的示例。
莎士比亚接受的小学教育大概会使罗宾逊爵士感到很震惊。学校的学生们被要求通过重复的背诵来学习上百种拉丁文的修辞方法。他们还要熟悉那些跟他们生活经验毫无直接关系的古代文章,如塞内卡和西塞罗的作品。历史上没有关于莎士比亚是否喜欢上学的记录,但是很显然,学校并没有压制他的创造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有史以来著有伟大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而且按照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雷克斯·吉布森(Rex Gibson)的说法:“莎士比亚在学校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他的戏剧性思维的推进力,即是我们现在认为毫无价值的背诵和不断的练习。”
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出生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曾在一所传统学校上学,成绩优异,尤其擅长英语和拉丁语。加入披头士乐队以后,他说:“我热爱文学。在创作Eleanor Rigby的时候,我尝试把它写成一首好诗。”
达尔文在1844年写给他的好友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的书信中明确指出,他的伟大顿悟来自对事实的系统性积累:
加拉帕戈斯生物的分布对我的触动如此之大……我决定开始无差别地收集任何一种证据,其中也许就会包含物种的本质属性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收集证据——最终那一,丝曙光降临了,而我基本上相信了(与我先前的想法非常不同)物种不是(这如同在对一场谋杀认罪)一成不变的。
拥有两百多项注册专利的多产发明家雅各布·拉比诺(Jacob Rabinow)在接受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采访时被问及创新性思维有什么必要条件,他回答说,最重要的条件是拥有一个装满了知识的大数据库。他说:“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你必须储备大量关于音乐的知识……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孤岛上从没听过音乐,那你不太可能成为贝多芬……你可能会模仿鸟叫,但是你不可能写出第五交响曲。越早着手构建这个数据库越好。你能够在存储了大量信息的氛围之中成长……人生开始阶段出现的一个小小的差异如果持续40年、50年或者80年,将会累积成巨大的差异。”
一名好的教师会帮助学生制造这种氛围。他们能主动地引导孩子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将消遣性好奇转变为认识性好奇,这样才能开始建立那个能够使创新变成可能的数据库。
误解3:学校应当传授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
1946年,荷兰心理学家、国际级象棋大师阿德里安·德格鲁特(Adriaan de Groot)进行了一项改变了科学界对学习过程的看法的实验。他向被试展示了一张象棋棋盘,上面摆放了一些棋子,并让被试感到棋局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展示只持续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他要求被试按照记忆进行复盘。象棋大师及以上级别的国际级象棋大师基本上能够准确无误地恢复棋子的位置,而好的业余棋手只能恢复大约一半左右,新手则更少,只有三分之一。
表面上看,象棋是一种纯粹的推理式游戏。然而象棋的核心其实是知识。象棋大师的大脑中记忆了更多的摆位,这样当他们看到棋盘时也会立刻识别出这些位置信息,这样就给他们更多的余地来思考下一步的走法(甚至下几步的走法)。威廉·切斯(William Chase)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又名司马贺)重新进行了德格鲁特的实验,但是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除了向被试展示一些可能的棋盘以外,他们还增加了一些随机生成的、不可能在真实对弈中出现的棋盘。象棋大师们对真实棋盘的复盘能力与在德格鲁特实验中所展示的相类似,但是对随机棋盘的复盘能力则与初学者无异。
象棋的关键与其说是抽象思维能力,不如说是与知识的紧密结合。高手在记忆中保存了上万张棋盘。类似的实验在不同的领域,如物理、代数和医学等领域被重复进行,每次的结果都一样。只要任务在专家的专业领域之外,他们就不再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技能都与特定领域的知识紧密结合。
换一种说法,心理技能不同于算法。算法在其适用范围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用考虑具体问题的对象。而学习能力则是从特定领域的特定知识中萌生的。所谓“特定领域的特定知识”就是事实(还包括文化知识,比如哈姆雷特的情节)。你的知识面越广,脑力活动的范围就越广,能吸收的新信息也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把培养学习能力置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