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小分队”口述史:对存在的绝望作出回应
“五一”假期读了“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的口述史《炽热的光及其他一切》(The Oral History)。附近有音乐节,低音炮轰鸣。人都离开家,扎堆去旅行,到处都喧嚣、混乱、缺乏注意力,超乎寻常的人流量构成各地的奇异景象,像是人群下意识地对缺乏希望作出回应。这种景况,和书中的氛围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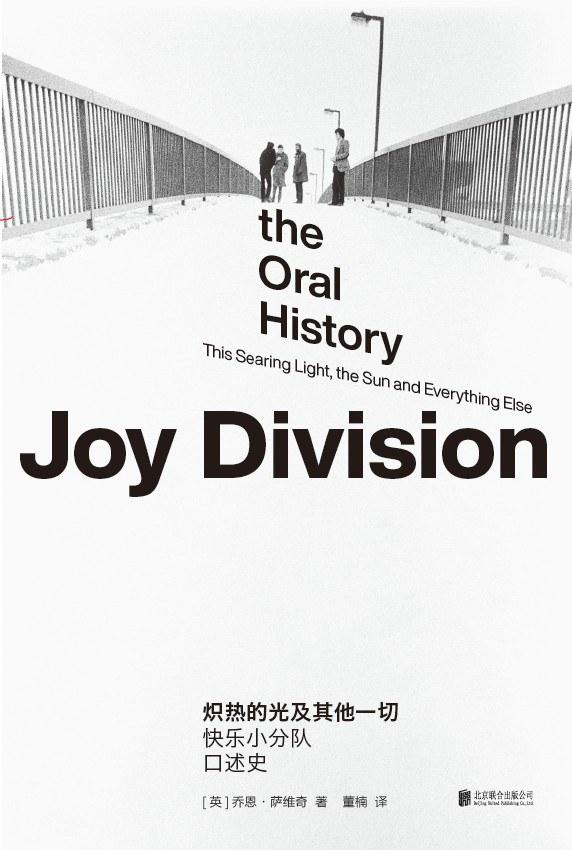
乔恩·萨维奇的这本新书,主角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时的一支英国摇滚乐队“快乐小分队”。他采访乐队成员及有关的众人,回忆这段飞星般的时光。书的真正主角,是早已死去的伊恩·柯蒂斯。他成就了乐队,也毁掉了乐队。他和伙伴们一起,对存在的绝望作出回应,最终不堪忍受痛苦,逃离了世界。
书从众人回忆城市开始。每个人都花时间讲述他们生长的城市,一路穿插媒体对这支乐队从小心谨慎到不吝赞美的评论。乐队成员均来自相隔一条厄韦尔河的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座英国北方的工业城市。他们长大的城市区域很少有树,天堂(通常以围墙花园的形态存在)是抽象的概念。
他们的城市像年老缺乏活力的宿根植物,外围还在生长,中心已经荒芜。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小孩,熟悉贫困和暴力,或许比中产更懂得自由。1976-1980年,乐队存在的几年像一个瞬间。瞬间被如梦似幻的回忆解构,破败的后工业城市,因为青春的关系现出虹彩。
到1980年5月18日伊恩死前,“快乐小分队”已经被捧上神坛。伊恩·柯蒂斯被视作英国的吉姆·莫里森,行过水上而无痕的耶稣。使他痛苦和难堪的病——癫痫,古代经常被视作神灵附体的表现,在当时依然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参与回忆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用清晰洗练的语言来讲述。伊恩死后,他们有漫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这种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使这本口述史呈现出日本版画的细腻纹理。一开始,大家都非常冷静,带着年长的人回忆青少年时光时特有的温柔和愉悦,讲述乐队从无到有的过程。或许是回忆过滤掉了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也可能“快乐小分队”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他们虽然号称是一支朋克乐队,却不危险、不恶心、不狂妄。他们像几个顺利毕了业找到工作,却依然容易在大白天进入梦境的人,迷迷糊糊又顺理成章地找到彼此,组了乐队,开始排练。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乐器的熟练使用者,但他们还是设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在简单的混乱中找到旋律和美。
这几个音乐的外行,因此顺利逃脱了他们这个阶层的生活轨道,因为感知到被设定好的未来而选择逆流游泳,逃到“工厂”俱乐部、录音室和租来的两套公寓里。逃到欧洲大陆,差一点就能逃到美利坚(可惜因为伊恩的死美国巡演被取消)。
用贝斯演奏旋律,把吉他解放出来做实验,类似于人机互动的鼓,加上伊恩·柯蒂斯——诗人、舞者、在台上极度坦率且能够一人分饰多角的主唱。这四个人建立起势均力敌,缺一不可的伙伴关系。他们太幸运,幸运到从来不需要讨论音乐。只要四个人在一起,每周排练两次,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新歌,就像置身于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梦境。

Joy Division乐队
他们不仅从不讨论音乐,也不谈别的和文学艺术有关的话题,无需形而上的理念或哲学支撑。摇滚有摇滚的理念,嬉皮有嬉皮的想法,朋克有朋克的坚持。大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历史和传奇。“快乐小分队”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他们的回忆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唯一一次自我意识的出现,是有人提到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大意是:“我们忽然想到,我们随心所欲更换的每一种造型,或许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但也仅此一次。到后来,这四个工人阶级的小孩不再奇装异服。他们打扮成正常青年的样子,穿衬衫、西装上台(甚至会打领带)。他们的头发短得不能再短。什么朋克精神,自力更生不依靠大厂牌,扶持本地音乐场景,反对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语言中都不存在。
即使有过这些念头,时间也早已把它们洗净,只剩下条索分明,永远难忘的事情。就像被真菌吃光了叶肉的树叶,叶脉的形状极漂亮,又非常脆弱,像永恒的一瞥,自由有形的存在。
在伊恩生病之前,大家都闭上眼,尽情享受延长的童年和青春期。这个时间段的特点是不反省,不会观察自己的心灵,不怎么需要休息。身体的疲惫和旺盛的精力是一对好朋友,不是造成精神内耗的最佳损友。他们只做,不说,到后来采访也不接受了,不再回应外界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是自己行动的绝对主宰。精神直接控制身体,使乐器发出极大的声音。他们沉浸其中,以至于当制作人马丁·汉内特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处理录音室作品,增加幽微的细节,使那些歌散发出不同于现场的阴郁气质,只会令小伙子们不满。
他们的天真和天分使人羡慕。四个人里面,只有伊恩的创作不是那么一气呵成。他是随身携带诗句重量的那个人,总是在阅读和写作,死前曾表示想退出乐队,买一家转角商店做书店老板,当一个作家。音乐自然发生的时候,他在写满诗句的纸上挑选合适的词句用作歌词。
一开始,写歌很困难。生病以后,伊恩发现写歌不再艰难。第一个句子出来之后,其他句子争先恐后地诞生。他像观看别人绘制的动画,目睹这个过程。他的生活也发生变化,有黛博拉和安妮克两个女人,一个女儿。乐队越来越出名。巡演很累,伴随无尽的小童式的恶作剧和新事物的刺激。四个成员最后都辞掉工作,变成全职音乐人。
音乐、工作、生活、爱情,原本泾渭分明的四种色彩,迅速地混合在一起。像有人为他们踩下加速器,使他们全心投入,最终无路可退。
书的前2/3是平平无奇的无忧无虑,但死亡就在那里,无人能够回避。对于伊恩之死,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多的看法叠加在一起,却无法给出一个真相。
唯一确定的是,他的死是这些人童年的结束和现实人生的开始。所有人都表现出懊悔,责怪自己当时太年轻天真或自私,对伊恩病情的恶化视而不见。只要伊恩说“没事,继续”,大家就当作房间里的大象不存在,继续活在梦境中。但其实他们从心底知道,一个人只要想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

Joy Division乐队
伊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众人的回忆,为“复杂”添上具体而丰富的色彩。那个只要站上舞台,就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人,还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于思考、温和有礼的人,一个无法拒绝别人的,有依恋和不舍的人。伙伴们注意到,就算在一个空间里相隔一米,伊恩也会对不同的交谈对象展现出不同的人格。
除非把他惹急了,他才会暴跳如雷(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两次)。基本上,你没法和他争吵,因为你说什么他都赞同。你没法知道这个人的真实想法,你只想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警方潦草地完成聆讯,朋友们拼凑出他死前的足迹。所有人一起(包括伊恩自己),把他逼到绝境。他认为自己可以忍受死亡,从一个牢房进入另一个牢房,但是无法忍受痛苦,也不能捕捉胜利。
他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捕捉胜利。没有人可以,因为延长的童年和青春不可能永续。即使他们听见了伊恩歌词里的挣扎和征兆,也没放在心上。团队里“最应该像成年人”的托尼·威尔逊(格拉纳达电视台主持人,“工厂”联合创始人),亦认为痛苦只是摇滚的一部分。音乐里的死亡意象,和真实的死亡之间并不相通。
在现实的维度,“快乐小分队”的确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他们声名鹊起,和另一支同为传奇的英国朋克乐队“性手枪”(Sex Pistols)截然不同。他们没有自毁倾向,像孩子一样地玩闹,目的不是激怒任何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受众相当地识货。他们既能够欣赏彼得·萨维尔设计的怪异专辑封面、演出海报,也能听出这不是一支“冒牌货”乐队,辨别出他们不是沽名钓誉之徒,每个成员都有独特的东西。那个跳着近乎癫痫发作的灵魂之舞的主唱,货真价实地在舞台上吐出肺腑,向大家展示血污的心肝。
这种景象注定了在世间罕见。有多少艺术家,最后成了本人艺术形象惟妙惟肖的模仿者。他们模仿自己青年时的形象。更多的人连模仿都不能够了,只能一边计算着出场费和出场次序,一边尽力满足观众的怀旧愿望。
“认识开始的第一个信号是求死的愿望。”喜欢卡夫卡的伊恩·柯蒂斯,一定读到过这句话。但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据此来理解他的死,或者浪漫化他的死亡。
死就是死,和生一样严肃。尽管经常被涂上黑色幽默或荒诞的色彩,它依然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
因为他的死,活着的人开始像成年人一样反思自己。只有离开童年的人,才有可能去观察它,然后感到悲伤。
和任何有关摇滚的书一样,这本书也让人感到悲伤。悲伤若能表达,有人可怀念,还不算太坏。若是集体失语,小丑横行,连悲伤的感觉也被消解,就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