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留存快乐的童年?丨海浪电影周沙龙活动
童年就像一张白纸,任意在上面留下色彩,等到这些印迹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显现出自我的模样,这张图画就永远留在个人的生命中。
5月26日,在阿那亚蜂巢剧场举办的沙龙“我们都是孩子——如何留存快乐的童年”对谈中,写作者、媒体人、《母职难题》节目主讲人泓舟,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老师、猫科动物之友、《百年孤独》译者、儿童文学爱好者范晔,看理想《漫游全球博物馆》主讲人姜松,何萍所和田巧云的第三个儿子、作曲及音乐制作人、音乐肖像、寻谣计划发起人小河,四位嘉宾从音乐、文学、博物教育等角度切入,倡导我们应以一种非功利的导向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同理心。

“我们都是孩子——如何留存快乐的童年”对谈现场(主办方供图)。
“留存”是大人特别有的概念,孩子没有
快乐的童年需要去留存吗?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走下去的童年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力量?
面对这一提问,小河从音乐教育在生活中的作用谈起。小河认为,“留存”是大人特别有的概念,孩子没有。从这个角度而言,艺术教育也是大人的愿望,施加在孩子的身上。在小河看来,孩子应该尽量像孩童,让孩子像孩子本身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他所接触到的最好的教育,艺术也是这样,音乐不应该是孩子的负担,音乐是最能够让人体会最超越生活、超越生命,超越我们俗世欲望的东西,就是让人瞬间可以提升的艺术形式,也是人类中最美妙的东西。
在过去一些年中,小河一直在进行着“寻谣计划”,寻找中国过去的童谣。在小河看来,新的东西是每时每刻都有产生的,这个世界就是新的,世界永远在创新,包括童谣。为什么“寻谣计划”聚焦在这片土地上即将遗失的老的童谣?小河认为,音乐包括民谣里面的歌词其实都有文化基因,我们如果觉得新的就好,老的就不好,因为这样的观念错失跟未来的连接,其实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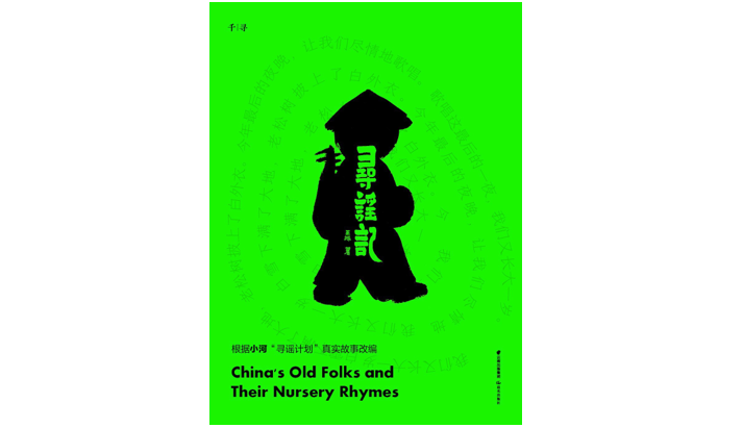
《寻谣记》,王烁(anusman) 著,千寻丨晨光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在北京发起“寻谣计划”的时候,小河只想做一个公共艺术项目,“音乐不是目的,音乐是手段和通道,目的其实是让我们走进老人,从四合院中心出去的老人重新回到这个主舞台,让他们在这个城市最活跃的地方重新连接,也让人们看到他们还在……新的要并存,但不一定老的要退出。”但在“寻谣”的过程中,小河发现了自己从未听过的好听的童谣。“寻谣计划”找到的第一首童谣是在玉渊潭公园,一个大爷从门头沟搬到城里,他小时候在门头沟生活,从卢沟桥跑着去上学,回来也是从卢沟桥跑回来,唱一首有关卢沟桥的歌。小河为此感到了惭愧,“有这么一首好听的歌你从来没有听过?就是那种惭愧。这种歌的歌词和旋律那么美,从来没有听过。年轻的时候我们只听西方的,只听摇滚乐……为什么这片土地上有的东西,我们就觉得理所应当?”
大家需要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一样的东西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想象力?在《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一书中,范晔创造了许多动物,比如“方糖鲸”,每次在大海里面游一会儿,大海就会因为它的呼吸变得更甜一点。
活动现场,范晔提及自己曾经在西班牙马拉加的毕加索故居博物馆买到的一张明信片上所写的毕加索名言: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后来的人生中,不失落这种艺术家的才能或者潜质?这在范晔看来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范晔以自己在《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中创造的动物为例,在这本书中,范晔想象了几十种动物,前面一两种真的是实有其物,但他也将之变得与现实中的动物不一样。受博尔赫斯等西语作家的影响,范晔为每一种动物都加上了拉丁文学名,“有的地方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些恶趣味在里面。”

《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范晔 著,顾湘 绘,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范晔说,书中的“风铃狮子”,直译的学名应该是“庄子狮子”。《庄子·齐物论》有一段专门描写天籁、地籁、人籁,风吹到不同地方都会发出不同声响,这对范晔影响很大,他也因此想象了一头狮子:这种狮子的鬃毛是中空的,上面有数不清的小洞,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窝。微风的时候,大风的时候,狂风的时候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像湍急的流水声,像迅疾的飞箭声,像粗暴的呵斥声,像细弱的呼吸声,像放声喊叫,像嚎啕大哭,像山谷回音,像小鸟嘤嘤,前面呜呜呜地唱着,后面呼呼呼地跟着。一头风中奔跑的风铃狮子,其实就是一台高速行驶的巴洛克音乐会——因为每根鬃毛都是空的,奔跑起来就成了音乐会。在写学名时,范晔并没有真正用拉丁文拼出风铃,写的是“庄子狮子”,原因正在于此。
还有一种动物是“洞穴企鹅”,洞穴企鹅生活在地下一百至一百五十米的波浪状的洞穴中。因为常年在地下生活,视力严重退化,嗅觉却十分发达。它们比嗅觉更发达的是想象力——每一只洞穴企鹅都是幻想艺术的大师,它们的幻想作品只有一个主题:大海,“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来想象大海。”范晔请画家画出洞穴企鹅的图,一开始,画家画了一直沉睡在大海深处的幼年企鹅,但范晔认为得修改一下,把小企鹅涂掉,画一只成年的企鹅,“因为大家小的时候有幻想的能力是很正常的,如果到了成年以后,成年企鹅还能够幻想,就更加难能可贵。”
在范晔看来,这样的幻想能力其实正是成年人的一种需要,这种幻想能力有着各种形式,有的人是音乐上的,有的人是文学阅读或者其他方面上的,“大家需要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内心的避难所。”避难所听上去似乎是消极的,但范晔认为,消极也是一种能力,而且是很高级的东西,“我们今天特别喜欢追求明确的、准确的、有时间节点的东西,但能不能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种暧昧难分、多少有点混沌的状态,我们往往视之为天然未完成的状态。”
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些留白
泓舟认为,如果将文学视为是无形的避难所,那么,博物馆可能就是有形的避难所。那么,如何在富含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中,连接自己的想象力呢?
姜松认为,对图像的解释能力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激发孩子对图像的兴趣,也就得到了博物馆所想要达成的目的。在18世纪中期,公共博物馆在西欧国家出现,一个最早讨论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对小孩开放博物馆?因为孩子很可能因为不懂而四处乱跑,甚至将文物打坏。但最终的讨论结果是:不光要对他们开放,而且要义无反顾地欢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进入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对某一件物品产生兴趣的时候,他们的领悟能力、解读能力完全超出大人的想象。
近年来,文博热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很多人前往博物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打卡拍照,但回到家里,真正沉淀在心里的会是什么呢?
姜松表示,从广义上来讲,博物馆总共有四大部分,这跟博物馆的分类有关。我们带孩子去博物馆究竟是看什么?就是了解四个主要方向。比如自然博物馆、综合博物馆,还有画廊、科技馆等,让孩子产生兴趣的点在哪里?姜松认为,关注每个孩子个体的兴趣在哪里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兴趣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完全持续下去。姜松认识很多孩子,把艺术看展作为一生的爱好。在溯源调查的时候,姜松发现,他们喜欢艺术,喜欢看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某一次博物馆经历,产生了好奇心,好奇心就是爱好,进而激发成为了动力,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一件展品背后的信息。

电影《博物馆奇妙夜》(2006)剧照。
“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进博物馆,走进这个时代精神的避难所。”泓舟认为,不管是文学、音乐还是博物馆,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在我们生活中有一定的留白,我们才能真正有时间、有精力静下心来欣赏,产生动态或者静态的互动和接触。在泓舟看来,成年人的时间都很繁忙,被排得很满,孩子也是如此,除了睡觉以外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培训班、辅导班、作业充满,但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些留白。
“不管是音乐、文学作品还是博物馆、历史、文化,这些都是每天存在于我们二十四小时日常中,我们用日常抵抗生命中的无常,这一点是我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泓舟如是说。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
